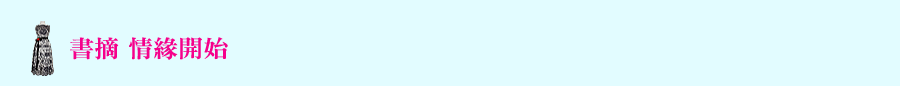|
今天一早走出家門時,我暗忖著,至少九月是個重新開始的好時機。九月初總是比一月更讓我感覺到煥然一新。穿越寧靜谷時我一邊想,或許這是因為過了陰溼的八月,九月往往令人感覺新鮮和清朗。
朝著希斯公園爬上山丘時,「古董服飾村」新上好漆的招牌映入眼簾,我放任自己沉浸在短暫的樂觀心情中。我開了門鎖,從門墊上拿起信件,開始為正式的開幕派對做準備。
我不停地工作直到下午四點,從樓上的儲藏室挑選衣服,然後把它們一一放在橫杆上。當我把一件一九二○年代的茶會洋裝掛在手臂上時,另一手情不自禁在它厚厚的絲緞上撫摸著,指尖觸碰它複雜精細的串珠和完美的手工縫線。我告訴自己,這就是我熱愛古董衣的地方。我愛它們美麗的布料和精緻的作工,也喜歡了解它們在製作過程中用了多少技術和藝術技巧。
我瞥了手錶一眼。距離派對開始只剩下兩小時了。要來採訪我的記者已經遲到超過一個小時。我甚至不曉得他是哪家報社的。昨天和他在電話上簡短地通過話,只記得他的名字是丹,還有他說三點半會到這裡。我的惱怒轉變成驚慌,猜想他可能不會來了,可是我需要媒體報導。
此刻我正在整理掛在正式服裝橫桿上的晚宴服,擺好包包、腰帶和鞋子。我把手套放進手套籃裡,人造珠寶飾品放在天鵝絨托盤上,然後,在角落的架子上,高高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擺上三十歲生日時艾瑪送我的帽子。
我往後退,凝視著那頂造型奇特的古銅色草帽,它的帽頂似乎向上捲起無限延伸。
「我好想妳,艾瑪,」我喃喃地說,「不管妳現在在哪裡……」一股熟悉的刺痛感襲來,像是一根長扦刺在心上。
身後,一陣急切的敲門聲傳來。玻璃門外站著一個約莫和我同年紀或比我年輕一點的男子,體格高大健美,還有一雙灰色大眼和亂蓬蓬的深金色鬈髮。他讓我聯想到某個有名的人,但我想不起來是誰。
開門讓他進來時,他露出大大的笑容說:「我是丹‧羅賓森。抱歉我來晚了一點。」我壓抑著沒說他其實遲到很久了。
「喔,我有時間。」我打斷他的話,「真的,只要你不介意我們談話時我一邊工作。」我把一件海洋綠的雪紡酒會禮服掛到絲絨衣架上。「你說你是哪家報紙?」我從眼角餘光注意到,他淡紫色的條紋襯衫和斜紋棉布褲的鼠尾草綠並不是很相稱。
「我們是新的免費報紙,一週出刊兩次,叫做《黑與綠》──黑石南與格林威治快報。這份報紙才上市兩個月,我們還在擴充我們的發行量。」
「任何報導我都很感謝。」我說,一邊把那件禮服放在日間服飾橫桿的最前面。
丹環顧店內,又說:「店裡真漂亮而且明亮。不會讓人感覺這裡賣的是老東西……我是說,古董。」他修正自己的用詞。
「謝謝你。」我啼笑皆非地說,不過我對他的觀察倒是心存感謝。
當我俐落地剪掉包裹著幾朵白色愛情花的玻璃紙時,丹透過窗戶往外看。「這個地點很棒。」
「我就是這樣發現妳的。」我把花插進一只高高的玻璃花瓶時,丹這麼說。「我昨天走路經過,看到妳……」他從長褲口袋裡拿出一個削鉛筆器,「正準備開店。我想應該很適合當成週五報紙的專題報導。」他在沙發上坐下,我發現他穿著不成對的襪子,一只綠色,一只褐色。「不過我對時尚不是很感興趣。」
「是嗎?」我禮貌地說。他用力地轉了鉛筆幾下。「你不用錄音機嗎?」我忍不住問。
他檢視著剛剛削尖的筆尖,然後對它吹氣。「我比較喜歡速記。那麼,好吧。」他把削鉛筆器放回口袋。「我們開始吧。所以……」他用鉛筆撥弄著下唇。「我應該先問妳什麼好呢?」他如此缺乏準備真是令我驚愕,但我試著不要表現出來。「我知道了!」他說,「妳是本地人嗎?」
「我是。」我折疊著一件淺藍色的喀什米爾毛衣外套。「我在靠近格林威治的艾略特丘長大,但過去五年一直住在黑石南區的中心,靠近地鐵站的地方。」我想起我那間有著迷你前院的鐵路工人小屋。
「地鐵站。」丹緩緩地複述著。「下一個問題……」這個訪問會花上很長時間,而我現在最欠缺的就是時間。「妳有時尚方面的背景嗎?」他問,「讀者會想知道這一點嗎?」
「呃……可能會吧。」我告訴他我在聖馬汀藝術設計學院拿到時尚史學位,還有在蘇富比公司工作的經驗。
「事實上,我不久前才被升為服裝和紡織品部門的主管。但後來……我決定離職。」
丹往上看了一眼。「即使妳才剛升職?」
「對,」我轉了一下念頭,我說得太多了。「是這樣的,我幾乎是一畢業就在那裡工作,所以我需要……」我瞥向窗外,試著平息猛然襲來的情緒波濤。「我覺得我需要……」
「一段休息時間?」丹問道。
「一個……改變。我在三月初休了一陣子的假。」我把一串香奈兒人造珍珠項鍊掛在銀色人體模型的脖子上。「他們說會保留我的工作到六月,但五月初我看到這裡的店面要出租,於是決定冒險嘗試,自己來賣古董衣。這個想法我已經醞釀好一段時間了。」我補充道。
「一段,時間。」丹輕聲複述著。這幾乎稱不上是「速記」。我偷偷瞄了一眼他怪異潦草的筆跡和縮寫。「妳的貨是從哪裡找來的?」他看著我問,「還是這是商業機密?」
「倒也還好。」我把Georges Rech咖啡歐蕾色的絲綢上衣鉤子扣上。「我從倫敦以外一些較小的拍賣行進了不少貨,也向專業的交易商以及我透過蘇富比認識的一些私人收藏家買東西。我也在古董展覽會、eBay上找貨,還去了法國兩、三趟。
「你可以在那裡的鄉鎮市場找到美麗的古董衣,好比這些刺繡睡衣。」我舉起其中一件。「我是在亞維農買到的。它們不會太貴,因為法國女人不像我們英國人這麼熱中古董。」
「古董衣在我們這裡變得相當受歡迎,是嗎?」
「非常受人歡迎。」我很快地把幾本一九五○年代的《Vogue》雜誌像扇子般攤放在沙發旁的玻璃桌上。「女性想要個性化的衣服,而不是大量生產的商品,古董衣正能滿足她們這項需求。穿著古董衣代表了獨創性和鑑賞力。我的意思是,一個女人可以在High
Street上用兩百英鎊買一件晚禮服,」我繼續說,已經進入接受訪問的氣氛中,「隔天就變得一文不值。但是,她用同樣的金額,可以買一件料子很華麗的衣服,不會和別人撞衫,而且只要好好保護,實際上還會增值。就像這件。」我抽出一件Hardy
Amies一九五七年墨藍色的塔夫綢晚宴服。
「很迷人,」丹說,看著它纖細的繞頸緊身上衣和下面的多片裙,「妳會以為這是新的。」
「我賣的每一件東西都處於完美無瑕的狀態。」
「狀態……」他再度振筆疾書,念念有詞。
「每件衣服都水洗或是乾洗過。」我把衣服放回橫桿上時說,「我有一位很棒的裁縫師,幫我做大規模的修理和改造,小規模的我可以在這裡自己動手做。後面有一間小『密室』,裡面有一部縫紉機。」
「這些東西售價多少?」
「從十五英鎊的手捲絲巾到七十五英鎊的棉質日間服裝,還有兩百至三百英鎊的晚禮服與一千五百英鎊的高級設計師服裝都有。」我拿出一件絲絨寬管女長褲,上面有果汁汽水般粉紅粉綠的迷幻圖案,「這套衣服是Emilio
Pucci的。買這件幾乎可以肯定是用來投資而不是用來穿的,因為Pucci就像是Ossie
Clark、Biba,以及Jean
Muir,非常具有收藏價值。」
丹說:「瑪麗蓮‧夢露很喜歡Pucci,她是穿著最愛的綠色Pucci絲質禮服下葬的。」我點頭,不想承認我並不知道這一點。
「那些很有趣。」丹對著我身後牆上掛著的衣服點了個頭。
「我把這些掛出來是因為我好愛它們。」我解釋,「它們是五○年代的晚禮服,但我都叫它們『杯子蛋糕』禮服,因為它們是這麼的迷人和輕薄精巧。只要看著它們,我就很快樂。」
這大概是我現在所能擁有的最大快樂了,我陰鬱地想著。」
──古董衣,啟動了過去,現在和未來......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