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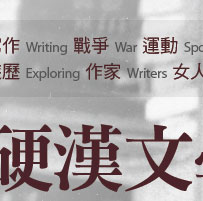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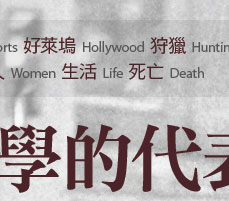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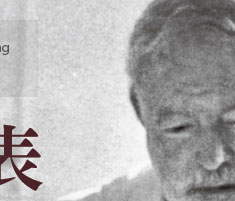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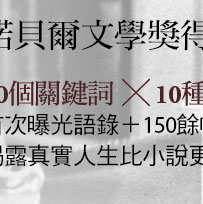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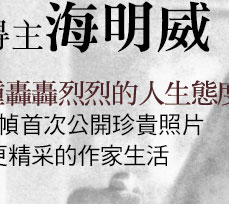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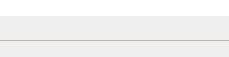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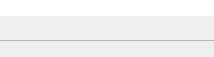


編者前言
他的熱情與矛盾──你不知道的海明威
文:本書編者A. E. 哈奇納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初識海明威。當時鬻文維生的我受某雜誌之託,要找海明威寫一篇蠢文章。我之所以鬻文維生,是因為在空軍服役四年後,我決定拿著優渥的遣散費在巴黎退役。當時美金是強勢貨幣,拿美金在巴黎非常好過日子,況且我正和巴黎歌劇院一位年輕的抒情女高音談戀愛,她還提議我搬到她位於巴黎高級郊區納伊的住處同居。
這種快活日子唯一的問題是,當我在巴黎耽溺逸樂之際,原本屬於我的編輯職位很快被在美國退役的勤奮軍人給占走。我昔日軍中袍澤亞瑟.戈登(Arthur Gordon)在當時頗富盛名的《柯夢波丹》擔任編輯,那時《柯夢波丹》仍以文學為主,還未被後來的總編輯海倫.葛莉.布朗(Helen Gurley Brown)搞爛。我在巴黎快活過日子的兩年,亞瑟數次邀請我去該雜誌擔任編輯;不過,等我終於決定回美國,當時幾乎盤纏用盡,甚至僅搭得起「法蘭西島郵輪」的二等客艙,而這時亞瑟和其他編輯也無法提供任何職位給我這個美國前少校、後來卻在巴黎納伊地區耽溺墮落的哈奇納。
想到自己走投無路,必須回聖路易市的法律事務所,繼續做「兵役委員會」還沒接受我的從軍申請把我解救出來之前的那份工作,我就憂心忡忡,幸好熱心的亞瑟見我可憐,幫我找了份差事:他給了我《柯夢波丹》仍屬文學性雜誌那輝煌的幾年當中,曾替該雜誌撰文的作家名單,要我找出這些人,設法請他們繼續供稿給雜誌社。這份名單的人物個個都是當代文壇巨擘,看得我甚感惶恐:女作家桃樂西.派克(Dorothy Parker, 1893-1967)、辛克萊.路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艾德娜.費爾柏(Edna Ferber, 1885-1968)、詹姆斯.桑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芬妮.赫斯特(Fannie Hurst, 1885-1968)、恩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 1905-1970)、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羅伯特.班奇勒(Robert Benchley, 1889-1945)。除了實際開銷可報帳,酬勞是每邀請到一位作家可得到三百美金。這樣的報酬不算優渥,不過,我已別無選擇,要不將就點接受,要不,就是默默回聖路易市,加入我與泰勒(Taylor)、梅爾(Mayer)、雪夫林(Shifrin)和魏勒(Willer)合夥,但參與不到兩年後就壯烈退出的法律事務所。
一開始,光想到要和名單上這些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聯絡,並且說服他們念在與雜誌的舊交情提筆賜稿,我就畏懼不前。然而,出乎意料,我發現這些在文壇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多半將作品寄給經紀人或所屬出版商,幾乎未曾被特定刊物邀過稿,因此,即使盛名如他們,發現自己受出版社青睞而直接邀稿,莫不格外榮幸,所以我的確成功獲得幾位文壇巨擘的首肯。譬如,需款孔急(這點令人遺憾)的桃樂西.派克答應替我寫一篇關於無聊猜字遊戲的短篇小說,後來我們甚至成為摯友多年,直到她過世。艾德娜.費爾柏自從德國殘暴政權出現,就「冰凍」多年,經我邀請,她竟願意破冰重拾如椽大筆,替我撰寫一篇小說。如同桃樂西,她和我也維持多年聯繫。事實上,我們在她位於紐約市雪莉─荷蘭飯店的住處初次見面後數月,她就邀請我參加由她做東的晚宴,那次聚會令人難忘,重量級賓客包括:喬治.考夫曼(George Kaufman, 1889-1961)、摩斯.哈特(Moss Hart, 1904-1961)、亞歷山大.伍考德(Alexander Woollcott, 1887-1943)、基蒂.卡立斯雷(Kitty Carlisle, 1910-2007)、格魯喬.馬克斯(Groucho Marx, 1890-1977)、瑪麗.艾斯特(Mary Astor, 1906-1987)、海倫.海絲(Helen Hayes, 1900-1993)和羅伯特.班奇勒。在這份邀約作家名單中,只有約翰.奧哈拉和威廉.福克納斷然拒絕我。
名單中我毫無意願接觸的人是海明威。對我來說,他比其他作家更令人畏懼,不只因為他是文壇巨擘,更因為他是當代極富聲望的社會名流。他的「豐功偉業」,如狩獵野生動物、外海釣魚、參與鬥牛比賽等事蹟廣披於媒體,還經常被渲染誇大。走筆至此,我想起多年後我們在紐約著名的史托克俱樂部小酌,還沒被店東薛爾曼.畢林斯禮(Sherman Billingsley)邀請到貴賓專屬的「犢室」前發生的一段軼事。吧台尾端有個酒醉男子離開他那群夥伴,踉蹌來到海明威面前,杯子高舉到敬酒位置,口齒不清地說:「你知道美國最重要的三個人是誰嗎?是艾森豪將軍、海明威,以及湯姆.柯林斯(Tom Collins,雞尾酒)!」
自從我高中英文老師希爾妲.列維(Hilda Levy)介紹我看尼克.亞當斯(Nick Adams)系列的海明威自傳體短篇小說後,我就對海明威景仰不已。我最喜歡的一篇故事是《拳擊手》(The Battler),沒想到二十年後我有機會替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一九五六年劇作家」節目將這故事改編成劇本。這齣劇不僅開啟我的劇作生涯,也奠定男主角保羅.紐曼的演藝事業。我讀過海明威的所有著作,看過根據他著作改編的每一部電影。事實上,在戰爭期間,我就是在所屬的空軍反潛司令部第十三聯隊駐紮地的黎波里(Tripoli)的飛機棚,觀賞由賈利.古柏和英格麗.褒曼所主演的《戰地鐘聲》。
「你為什麼不跟海明威聯絡?」亞瑟想知道答案。「《柯夢波丹》在海明威的《雖有猶無》(To Have and Have Not)出版前曾幫他連載過這本小說,基本上我們的關係應該不錯。」
「可是,亞瑟,你是要我請他寫一篇談文學之未來的文章啊。我實在無法開口要偉大的海明威寫這種蠢東西,他會殺了我的。」
「這系列的撰稿人都大有來頭,包括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談建築的未來、尤金.歐尼爾(Eugene O' Neill)談戲劇之未來、亨利.福特二世談汽車之未來、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談芭蕾之未來。你就別膽怯了,快把你那長滿雀斑的屁股移往古巴,否則你就等著回聖路易市,將鼻子埋在《美國法學釋義》(Corpus
Juris Secundum)這種書裡吧。」
於是,1948年我抵達古巴首都哈瓦那,很孬種地寫了一封短箋給海明威,告訴他我人就在當地,身負一樁難為情的任務:懇請他針對文學之未來賜稿一則,不知他能否撥冗回覆,就算拒絕也行,這樣我才能保住在《柯夢波丹》的卑微差事?我請投宿的「國家飯店」幫我安排信差將短箋送給海明威。當時他住在哈瓦那郊區一個稱為「保羅之聖法蘭西斯科」(San Francisco de Paula)的小村落。
當天下午,我房間的電話響起,另一頭傳出熱情的聲音:「哈奇納先生嗎?我是海明威,我收到你的信了,不會讓你空手而回的。若被赫斯特出版集團攆出來,應該像被痲瘋病院扔出來一樣丟臉吧。五點鐘左右要來和我喝一杯嗎?有間酒館叫『佛羅里達』,計程車司機都知道那裡。」
就這樣,直到他去世,我們開始了一段到處尋求刺激的十四年友誼,這段歷程就記錄在我的回憶錄《海明威老爹》(Papa Hemingway)中。而最近剛出版的《親愛的老爹、親愛的哈奇》(Dear Papa, Dear Hotch)則收錄了首次見面之後的早期書信往來。海明威後來的確賜稿給《柯夢波丹》,不過主題不是關於文學之未來,而是一則短篇故事,這故事後來發展成小說《渡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這時,亞瑟已替我在雜誌社弄了個正式職位,於是我就陪著海明威到巴黎和威尼斯查證小說草稿的該地文字描述。
後來亞瑟被《柯夢波丹》開除,空缺由赫柏特.梅耶斯(Herbert Mayes)填補。他是個可憎自私、毫無品味的傢伙,曾在《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雜誌擔任編輯。他上任沒多久,我就離開《柯夢波丹》,成為工作不穩定的自由撰稿人,此後未曾再風光受聘於任何企業。自由撰稿的工作雖不穩,卻可以讓我為所欲為,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所以我經常與海明威出遊冒險。我們在巴黎的奧代伊爾區參加秋季的越野障礙賽馬,當地聖誕節的熱鬧氣氛使得這次出遊出奇地盡興。我們也去古巴首府哈瓦納外海的莫洛碉堡附近海域捕馬林魚;還去西班牙的潘普隆納參加奔牛節,親眼目睹兩大鬥牛勇士歐東內茲和多明昆捉對廝殺。另外,我們在美國愛達荷州的凱瓊鎮獵雉雞與綠頭鴨,在紐約參加拳擊賽,在洋基球場看職棒世界大賽。我們也經常聚首,討論由我將他的小說和短篇故事改編成劇本的相關事宜,譬如那週在他佛州西礁島住處的聚會即是為此目的。
我們所到之處,他和我、其他友人,甚至和沿途陌生人之間的對話,他對自己和別人行為、動物和魚鳥,以及周遭世界的觀察,精闢深刻,常讓我不由自主地想加以記錄。於是隨手可得的旅館信紙、紙巾、菜單、記事本、洗衣單的背面,都有我對他話語的紀錄。海明威非常健談,機智風趣,辯才無礙,自有主見,對人過目不忘,還能精確記得童年往事。
這些機智、風趣、犀利、冷靜、深具哲學性與啟發性的觀察和反思,部分收錄在《海明威老爹》一書中,不過第一次初稿修潤時,我刪除了一百多頁篇幅,所以許多他的觀察和反思在付梓的書裡無法見到。而現在我就是要把出版過以及未曾付梓的遺珠之憾,連同我收藏在抽屜底層那堆紙條的內容整理起來,另外集結成書。
這本書裡的許多話語都是海明威在旅行沿途與他人的交談。這些人包括在凱瓊鎮遇到男星賈利.古柏,在西班牙小鎮丘里亞納與英國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巧遇,在西班牙的馬拉加遇見美國女星洛琳.白考兒(Lauren Bacall),在紐約和出版商史基伯納(Charles Scribner Jr.)相談,在巴黎得見旅館業鉅子查爾斯.麗池(Charles Ritz),在威尼斯遇見年輕義大利女貴族阿德里雅娜.衣凡西雀(Adriana Ivancich),在紐約和女星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相見,在米蘭遇見英格麗.褒曼,在威尼斯的哈利酒吧與老闆西普利安尼(Giuseppe Cipriani)相見歡,在巴黎和威尼斯與琦琦.維泰爾(Gigi Viertel)不期而遇,在西班牙巧遇遊遍西班牙的爵士樂手比爾.戴維斯與夫人安妮,在紐約遇見傳奇餐飲人物土茲.秀爾(Toots Shor),在西班牙小鎮丘里亞納與巴克.藍漢姆將軍(General Buck Lanham)和印度寇屈貝哈(Cooch Behar)大君相見,在愛達荷州的海利鎮偶遇高中同學,在馬德里見到作家喬治.普林波頓(George Plimpton),在西班牙潘普隆納得見紐約社交名媛「苗條的海沃德」(Slim Hayward)、也就是後來的凱斯夫人(Lady Keith),在內華達州遇見著名藝術家沃爾多.皮耳士(Waldo Peirce),在西班牙舊王室所在地埃斯科里爾遇見女星艾娃.嘉娜(Ava Gardner),在威尼斯遇見費德瑞科.凱雀勒伯爵(Count Federico Kechler)。
就我所知,這些交談片段未曾出現在海明威出版的任何著作中;不過他這人說話經常重複,晚年更是如此,所以或許有些對話與他書中寫過的內容類似。
本書中各式各樣的語錄所交織出來的海明威,呈現出他過世後出版的各種傳記所沒有的面貌。他對其所處世界的喜怒哀樂,對不義與榮光的親身觀察所流露的易變、深刻、矛盾、熱情、詆毀與易感性格,是這些身後傳記無法捕捉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