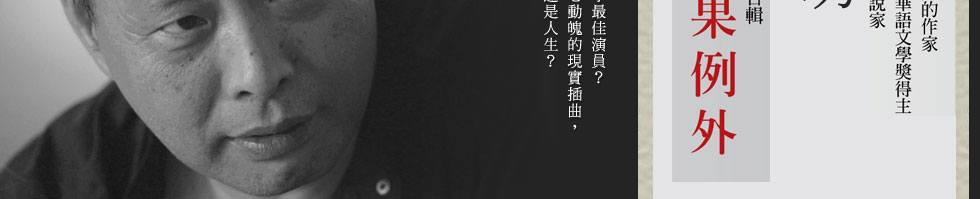我豎起雙耳,屏氣凝神,但一直沒聽到大隊伍嘈雜的腳步聲,沒聽到警車由遠而近的尖銳笛聲,沒聽到警隊指揮員通常在電喇叭裏發出命令的聲音……就是說,我等呵等,沒有等到任何希望。
我與鐵子只能依靠自己,嘗試逃跑的可能性。她在我的鼓動之下,借上廁所的機會,偷來一小塊碎玻璃,在夜裏割斷了捆她的繩子,也解開了綁我的繩子。她解繩子的時候嚇得手直抖,好幾次停下來,捂著胸口大喘粗氣,說她怕,好怕,太怕啦,我們還是認命吧?直到我氣得大罵蠢豬婆不知死活,直到我拿腳狠狠地踹她,她才顫顫兢兢繼續解下去。
繩子既然已經解開,就沒有回頭路了。她再一次聽我教導,使勁地點著頭,大概也明白了這一點。快天亮的時候,我們等來了看守人最困的一段,靠一張鋼筋防盜窗作工具,偷偷撬開庫房的門——這需要我們兩人抬著防盜網協同操作,就像扛著兩棵大樹當筷子,實在是工程浩大,費了近半個小時,累得我們滿頭大汗。但我們找不到合適的工具,不能不這樣以繁代簡。
要命的是,她實在太笨了,總是不得要領,在最需要一齊下力撬門的時候,她竟然丟下了手裏的巨型筷子,用袖口來給我抹汗。
「你豬呵?」我差一點罵出高聲。
「我怎麼了?怎麼了?」
「這是擦汗的時候嗎?」
「哦,對不起,我不知道……」
「用力,再用力!」
她哆哆嗦嗦更不知道如何用力了。
我額上的汗也更加洶湧。還好,天不絕人,我們總算撬開了門,總算溜下了樓道,甚至借一棵小樹翻過樓房外一道磚牆——線路都是鐵子白天暗中偵察過的。不料她關鍵時刻再次添亂,跳牆時竟傷了腳,大概是骨折或者脫臼,一跛一跛根本走不動。我差一點急得喊天,只好背上她朝前探步。但這時狗叫起來了,樓房裏電燈亮了,打手們朝著窗外大喊大叫,包括阿中的聲音都清晰可聞……我已經開始絕望。
「別管我了,你……」她在我耳邊急急地說。
「那不行,我不能把你丟下。」
「蠢呵?跑一個是一個。」
「要死就死在一起。」
「看不出你還很義道。」
「這樣一說,我就只能繼續義道下去。」
其實,我也明白,只要有一個逃出去,就可以去報警,就使槍匪們有所顧忌,另一個也才有得救的可能。但那一刻我似乎義道得很暈,反而把她摟得更緊。
「臭窩筍,臭窩筍!你聾了?你蠢呵?……」她在後面使勁地打我,撕我的頭髮,直到撲嗵一聲摔倒在地。打手們追上來,幾道強光照射著我們。
我睜不開眼睛,只是長長歎出一口氣,等待他們的發落。他們會重新捆綁我,重新給我蒙眼或者嘴裏塞布團,甚至一支手槍頂住我的太陽穴:一、二、三——他們如果害怕夜長夢多,不是不可能隨時下毒手的。奇怪的是,我久久沒有聽到動靜,甚至發現在場人都有些手足無措。不知什麼時候,我聽到一個人說:“導演,沒膠片了,算了吧?”
這句話令人費解。
接下來,我聽到了一道哨聲,聽上去也怪怪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我聽到有人鼓掌。
掌聲中,周圍的人都笑起來,一張張臉上綻開了花。疤臉漢子丟掉手裏的木棍,伸手來與我握一把手,又同鐵子握一把手,還幫我們拍打身上的灰。阿中哈哈大笑,指指我的鼻子,捂住自己的肚子一次次下蹲,笑得要滿地打滾的樣子。在一輛汽車強烈的車燈光柱裏,一個披著軍大衣的人提著電喇叭走來,對阿中高興地說:「OK,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剛才這一場追逃戲,比我預想的要好得多。可惜破門那一段沒機位……」他看了我一眼,發現我還在目瞪口呆,便過來握住我的手,「對不起,讓你受驚了。我來自我介紹一下吧,我是導演,叫孫建平……」
我覺得他面熟。事後我才知道,我確實見過他,就是皇家酒樓裏婚宴上的那個新郎,當然是偽裝的新郎。
「是這樣。」他遞給我一張名片,「我們正在拍攝一部實驗性電影,片名叫《風季》,完全是原型主義的探索。」
「你們這是怎麼回事?」我已經氣得七竅生煙。
「別生氣,別生氣,聽我慢慢給你解釋。這樣說吧,《羅馬十一點》你看過?那是義大利片,新聞紀錄手法。我們這個更進一步。主角多用原型,拍攝全用實景,不少情節隨機發展,多機位元全程偷拍。有些人,就像你吧,根本不知道自己入戲,這樣表演就更加自然。是不是?」
「你是說,你是說,這一切……都是拍電影?」
「是呵是呵,拍電影。最新潮的電影。」他不無得意地一笑。
我幾乎要哭了,「阿中你這個臭雜種,你……你他娘的跟我玩這一套?」我撲上去抓住阿中就打,打得他兩手招架,連連討饒,躲入孫導演的身後。「武哥武哥你聽我說,我看你平時對電影感興趣,一番好意讓你來玩一票。其實我同他們都說好了,對你不要真打,也不讓你餓著,天地良心……」
要不是幾個人阻攔,我非把阿中這傢伙一口吞下去不可。算下來,整整二十多個小時,我一直蒙在鼓裏,成了一個可笑的牽線木偶,任他們這些人算計著和玩弄著。我算是白怕了,白氣了,白傷心了,白義道了,還白白尿了兩次褲子。要是我一慌神做出不得體的什麼事,豈不是也會被他們拍個正著?「我操你大爺——」
我差不多哭了,一連罵了幾十句粗口,罵出了世界上最惡毒、最下流、最不堪入耳的話,罵遍了眼前所有微笑的惡棍。哭罵聲中我當然也有一絲慶倖。事情還好,只是虛驚一場和惡夢一場,我一條小命還在,還可以走路,可以吃飯,可以逛街,可以蹬自行車上班——要知道,身陷囹圄的時候,即使是平時最為令人厭惡的上班,包括在那個愚蠢編輯部主任手下的上班,對我來說也是無比幸福的回憶和嚮往。我沒料到這一輩子還可以大張旗鼓有聲有色地上班。
「你不要怪黃總。他只是贊助人之一。情節提綱都是我的設計。」孫導演給我披上一件大衣,遞給我擦臉的紙巾。
「你你你們這不是胡鬧嗎?」
「藝術麼,總得別出心裁不是?這是我有生以來最興奮的創意。你雖然受了點驚嚇,回頭一想,不覺得也是一次奇妙的體驗?」
「你怎不拿你老爹老娘來體驗?」我沒好氣地頂回去。
「我們充分考慮了你的條件,這一段戲,非你莫屬。」他用一大堆恭維話補償我,吹噓我的鼻型、身高以及正義感,正是他的藝術創作所需。至於他們事先無法向我交底,有不當和不敬之處,還望我海涵。他又說拍這種片子特別累,特別費錢,特別有風險,光是十幾個機位的隱藏和移動,光是長時間的耐心等待和各機位的靈機應變,就比拍戰爭場面還困難百倍……他大概想誇張他們的苦處,抵消我的一些怨氣。
我們走在返回樓房的路上。導演順便讓我見見他手下的人。我走到灌木叢後,看見了藏在灌木後面的攝影機,還有總攝影師。又走到一輛麵包車前,看見了架在視窗的另一台攝影機。車前兩個披著大衣的青年,正在收拾電線什麼的,沖我笑了笑。孫導對他們吆喝:「喂喂快收場,動作快點聽見沒有?小劉你磨蹭什麼?還想在這裏喂蚊子呵?」
「小劉」就是那個戴眼鏡的小白臉,幾次同我過不去的王八蛋,曾在大街上把我往死裏踢。我一見他就冒火,沖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突然發現他一臉微笑,才迷迷惑惑地穩住手。
我得記住:電影。
他放下手裏的一個木箱,拍拍我的肩以示和解,還塞來一張名片:「您能不能談一談自己的感受?」
我怒衝衝地說:「沒什麼感受。」
「好幾家報紙約我寫拍攝花絮,你一定要配合呵。這也是你出名的機會。」
「你站遠點,站遠點。跟你說,我這個人腦子有毛病,一走神就還會打人。」
他嚇得連忙退了一步:「好好,我們等下再談,等下再談。」
孫導笑著說:「你這種情況叫幻覺滯後。有些職業演員也這樣,一入戲就出不來了,好一段時間還會有幻覺。今天幸好是讓你演你自己,要是讓你演毛主席,那還得了?」
他們都沖著我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