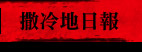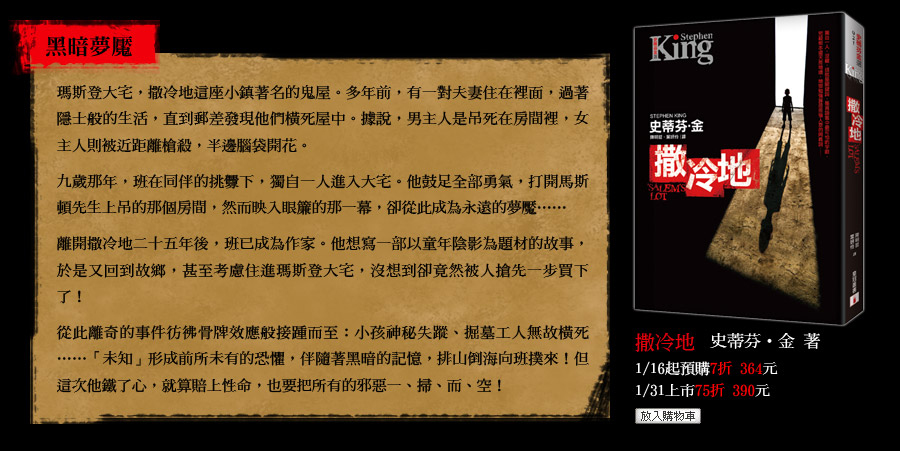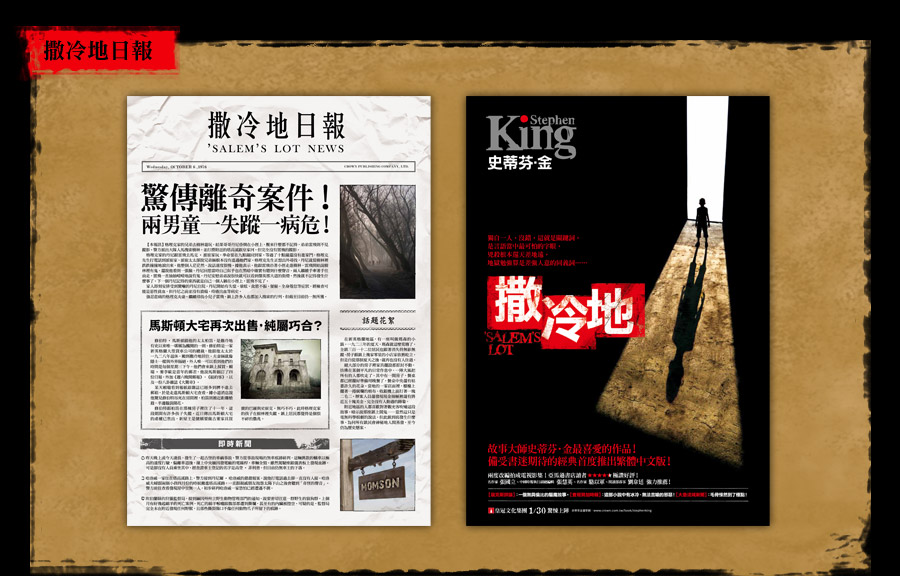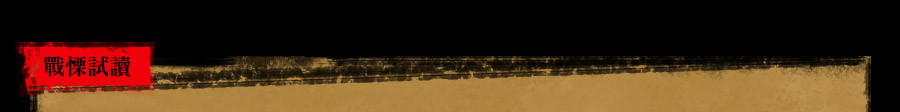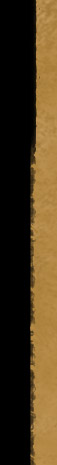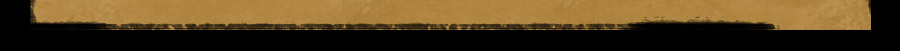如今讀來的「原點」感受──談史蒂芬.金的《撒冷地》
【文字工作者】劉韋廷◎文
《撒冷地》於一九七五年時出版,是史蒂芬.金的第二本小說。對金而言,雖然前一年推出的處女作《魔女嘉莉》頗受歡迎,但當時將金名氣一口氣推高的《魔女嘉莉》電影版尚未推出,是以《撒冷地》的成敗與否,仍對金接下來的作家之路有著極具指標性的影響。
所幸的是,《撒冷地》這本金自稱融合了《德古拉》與《小城風雨》(Peyton Place, 1957)的恐怖小說,在銷售上不僅順利延續前作佳績,甚至還入圍了一九七六年世界奇幻獎最佳小說項目,使金的地位因此更為鞏固,令本書繼《魔女嘉莉》電影版後,亦於一九七九年改編為三小時長的電視電影《午夜行屍》。而這部《午夜行屍》,也在經典恐怖片《德州電鋸殺人狂》、《鬼哭神號》的導演陶比.胡波打造下,入圍了愛倫坡獎最佳電視節目及三項艾美獎,獲得評論界的優異評價,此後亦曾另行改編為七集的廣播劇版本,以及新版電視電影等作。
或許你在閱讀《撒冷地》的前半段時,會感受到這本小說的時代性(事實上,就連金在本書的後記中,也曾提及這本七零年代的小說「在許多部分都有點過時」)。但若是細心思量,你便會發現這樣的感覺與其說是「過時」,不如以「復古」來形容會更為妥切一些。
正如金所提及的一樣,這本以「吸血鬼肆虐小鎮」作為主題的小說,其實巧妙轉化了《德古拉》的情境。在書中,神祕的陰森古堡,變成了一棟鬧鬼傳聞不絕於耳的廢棄大宅。而二十世紀的鄉間小鎮,則在城鄉發展的劇烈差異下,成為如同十九世紀化外之境般的存在。在《德古拉》一書中,吸血鬼造訪了當時最為進步的倫敦;而在《撒冷地》裡,吸血鬼則回歸至比起城市、顯然更適合他們生存的現代偏遠小鎮。
於是,就在這些相似且可供對應的元素中,才令全書擁有如此強烈的復古氛圍,同時也更進一步地讓金得以藉由本書,開始實驗其「小鎮生活作為社會及人類心理的縮影」的創作觀。
如果你是金的忠實書迷,肯定會對他筆下虛構的「城堡岩鎮」感到印象深刻。金不僅以城堡岩作為故事背景寫出多部作品,就連在他推出號稱是「城堡岩系列完結篇」的《必需品專賣店》後,也仍依依不捨地在其後多本著作中,不時帶領讀者回到城堡岩這個地點探望一番。
然而,就像金在中篇小說〈太陽狗〉前言裡提到的一樣,雖然在設定上,這個全名為「耶路撒冷地」、鎮民暱稱為「撒冷地」的虛構小鎮,與城堡岩各自位於緬因州的南北兩端,但對金來說,城堡岩其實就是沒有吸血鬼的撒冷地。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撒冷地》則讓我們看見金在剛成為職業作家時,努力以多線手法展示小鎮居民的生活面貌,並進一步地藉此呈現社會縮影,將各種隱藏在表面下的人際關係衝突,轉化為推展小說情節的寫作嘗試。
除此之外,就其它方面而言,《撒冷地》也是一本足以讓我們窺見金後來創作習性的縮影及起始之作。例如,這是一本金首次以作家作為主角職業的長篇小說,也是部金首度讓主角回到離開已久的故鄉,嘗試克服童年夢魘的作品。
雖然如今看來,與金後來精進的寫作能力相比,《撒冷地》一書在上述提及的特點部分仍未臻成熟,但諸如此類的故事元素,卻也得以強調出金在寫作能力上的演變脈絡,而這點,正是金的書迷不可錯過本書的最大原因。甚至,如果你是恐怖小說或電影迷的話,自然也不可錯過這本首度將「吸血鬼」與「美國小鎮」妥善融合,影響了後來無數好萊塢恐怖電影的濫觴之作。
關於這本《撒冷地》,還有一點頗值得一提。雖然本書是金早期的名作,但對台灣讀者來說,卻也是過去未曾發行過繁體中文版的遺珠之憾。但幸運的是,這回的《撒冷地》除了讓金的書迷得以一償宿願外,皇冠出版社更挑選了美國於二○○五年時推出的特別版作為此次的引進版本。在這本特別版裡,除了《撒冷地》的小說本文,還另行附錄了過去曾收錄在《玉米田的孩子》(Night
Shift, 1978)短篇集中,與「撒冷地」這個小鎮相關的兩部短篇作品。
其中的〈耶路撒冷地〉,是在《玉米田的孩子》中首度公開之作。本篇將故事時間點拉回十九世紀,並交代了撒冷地過去的黑暗歷史。雖說這篇小說與《撒冷地》的故事無關,而是一篇向霍華.菲力普.洛夫克萊夫特筆下「克蘇魯神話」系列小說的致敬之作,但在寫作手法方面,卻也採用了如同《德古拉》般的書信體作為體裁,並以不同的故事元素,讓人再度聯想到如同「城堡岩」系列般所會出現的情況。
至於另一篇〈夜荒荒心慌慌〉,則是金一九七七年首度於《緬因雜誌》(Maine)上發表的作品,故事時間點設定為《撒冷地》事件的數年後,並直接交代了這個小鎮後來的發展為何。由於〈耶路撒冷地〉於數年前曾以〈耶路撒冷之籤〉這個譯名收錄在《克蘇魯神話》一書中,是以〈夜荒荒心慌慌〉一篇,相信亦是許多讀者至今仍未曾讀過的短篇作品。
除了這兩篇短篇,這本《撒冷地》特別版最有趣、同時也是最具收藏性的部分,便是收錄了原本被刪去及修改的數十頁初稿內容部分。在這些刪除段落中,每一段的前頭都有金的補充說明,告訴讀者這些段落原本位於故事中的什麼位置。而透過這些段落,也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從初稿到定稿之間,一則故事可以產生多大的變化,甚至還能讓讀者實際揣想編輯與作家的合作方式,並對小說的創作過程有著更進一步的了解,亦與全書在如今讀來的「原點」般感受,擁有相互呼應般的效果。
在漫長的等待下,此刻你手上的這本《撒冷地》,不僅可以讓你看見一個引領恐怖文類數十年之久的作家風格原點,我想,光是那些讓人心動不已的特別收錄,便已經讓人覺得這樣的等待,的確是十分值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