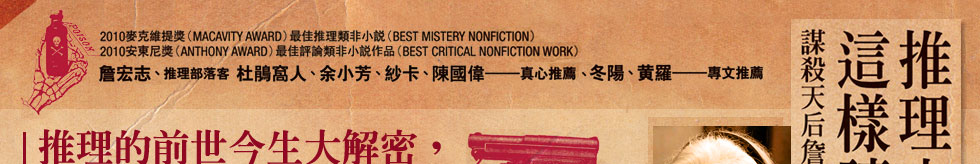一流的偵探小說,跟主流小說和廣義的犯罪小說有什麼不同?
一流的偵探小說同樣可以在一件事的危險邊際上運作,不過它跟主流小說和廣義的犯罪小說仍然不同。主要的差別在於,偵探小說有嚴謹的結構和一定的規則。我們會期待在偵探小說中看見:一起神祕的犯罪事件;一群犯案動機、方法工具和下手時機各有不同的有限嫌犯;一名業餘或專業皆可的偵探,以復仇之神的面貌前來調查刑案;到了故事最後案件偵破,水落石出,讀者從狡猾誘導但不失公允的線索中,經過一番邏輯推論,應當也能順利解謎破案。以上是我談到自己的作品時常給的定義,雖然不算錯誤,不過今日看來卻太過狹隘,比較適合用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所謂的推理小說黃金時期。不是所有凶手都混在一小群嫌犯中,偵探也可能遇到有名無姓或身分不明的對手,到最後主角偵探會藉由觀察和推理,當然還有大家公認的英雄特質,如聰明才智、過人的勇氣和體力等等來擊敗對手,讓對手難看。這一類推理小說,通常是英雄主角和他追捕的對象之間的衝突交鋒,凸顯的是身體互搏、心狠手辣和流血暴力,甚至會變成肉體的折磨。就算書中的推理成分很濃,但稱之為驚悚小說還是比偵探小說適合。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的○○七系列小說就是明顯的例子。但一本書要被稱為偵探小說,一定要以一個謎案為中心,小說到了最後,解謎破案的方式要合理且令人滿意,不能純粹靠運氣和直覺,應該要從書中儘管有意誤導卻仍如實呈現的線索中抽絲剝繭,推論出答案。
有人批評偵探小說模式固定,只是照公式寫作。這套公式如同給小說家穿上束縛衣,妨礙了創作的自由,而自由不正是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再說,為了維持固定的架構和情節,就會犧牲細膩的角色刻畫、生動的場景描寫,甚至還有故事的可信度。有趣的是,這套所謂的公式為各式各樣無以數計的著作和作家所用,而且很多作家認為,偵探小說的限制和規則與其說阻礙他們的想像力,不如說解放了他們的想像力。由此可見,若說受限於固定結構就不能寫出好小說,就好比說十四行詩必須限制在十四行(前八行加後六行)以內並遵守嚴格的押韻順序,所以不可能是好詩一樣可笑。況且,偵探小說並不是唯一必須遵守一定規則和結構的小說類型。珍‧奧斯汀的所有小說都有相同的情節:一名年輕美貌的淑女克服種種困難,跟心儀的男士結為夫妻。這是言情小說歷久不變的規則,但經過珍‧奧斯汀的妙筆,卻成了言情小說的大師傑作。
為什麼非謀殺案不可?
那麼,為什麼非謀殺案不可?
偵探小說的核心疑案不一定要是謀殺案,不過謀殺仍是一種獨特的犯罪活動,具有厭惡、執迷和恐懼這些原始人性的重量。一般來說,讀者對哪個不肖子在艾莉姑媽晚上喝的可可裡加了砒霜,比誰趁她在博恩茅斯安穩度假時偷了她的鑽石項鍊更有興趣。桃樂絲‧賽兒絲的《同學會之夜》難得沒有發生謀殺案,但有人試圖犯案。法蘭西絲‧法斐德(Frances Fyfield)的《石中血》(Blood from Stone)的核心死亡案則是一起引人注目又神祕難解的自殺案。然而,除了以背叛為主題的間諜小說外,正統推理小說中的核心犯罪案仍然絕大部分都是人力無法挽回或彌補的殺人案件。
我從賽兒絲和克莉絲蒂身上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從賽兒絲和克莉絲蒂身上學到了一個教訓。兩人一開始都選擇了怪裡怪氣的偵探,久而久之就完全失去了個人魅力。有鑑於此,我決定選一個不那麼異於常人的偵探,一開始他就失去了妻子和新生子,這樣就不需要描寫他的感情生活,這部分我想很難成功融入古典偵探小說的結構。我給了他無論放在男女身上我都會欣賞的人格特質,包括機智、勇敢(但不是蠻勇)、敏感(但不是多愁善感)以及謹言慎行。我認為如果這本小說會成為系列小說的第一本,這樣的人才是一個可信度高且有發展潛力的專業警察。系列偵探當然有一些好處,首先,已經確立的人物不用每次都重新介紹,也有風光的破案紀錄可增加人物的分量,還有一定的背景歷練和家族歷史,最重要的是,讀者比較容易認同他也願意追隨他。新出版的精裝或平裝小說的書衣,除了作者和書名以外,多半還會印上偵探的名字,這就是在對讀者保證:他們在小說裡一定會遇到熟悉的老朋友。
那麼其他角色呢?尤其是受害者和倒楣的嫌犯?